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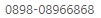
地址:山东省中欧体育·(中国)官方网站
电话:0898-08966868
传真:020-896-6868
邮箱:admin@zhonggudui.com
更新时间:2023-08-28 06:51:38
新文明的种子与土壤读过建生的书稿,让我敬畏之心油然而生。书的副题是“新乡村建设手记”,其实是一本“新乡村建设手册”,每一位有志于乡建理论和实践的人都该读一读。
乡村建设是一个老话题,也是一个新话题。一位名牌大学的博士,毕业后不在大城市工作,跑到农村,会让人深感困惑。很多人初闻“乡建”,可能联想到支教、扶贫、慈善,乃至上山下乡。不仅外人如此,甚至有些志愿者也会有这种想法。
社会实践没有恰当的理论指导,是盲目的,有时会适得其反,以为是帮忙,其实是添乱。建生的著作中,包含了大量的理论建设。
关于为什么乡建,建生追溯到晏阳初。实话说,我是在接触到乡建之后,才开始深入了解晏阳初的。这是一位世界伟人,是一位被严重忽视的先知。
1926 年以后,晏阳初以河北定县(今定州)为根据地,开始了史称“定县实验”的综合性社会改造。晏阳初把当时中国人的问题概括为“贫弱愚私”,并认为,其根本的解决方式在于教育。他提出以学校、社会、家庭“三大方式”,同时进行文艺教育、生计教育、卫生教育、公民教育“四大教育”。因为农村的问题不是某一个方面的问题,而是全局的问题,不能头疼医头、脚痛医脚,必须谋求综合的解决之道。(第4页)这种“、经济、文化中欧体育、卫生连环并进的农村综合改造”(第12页),在我看来,正是一种在文明层面上的社会改造。
鸦片战争之后,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巨变。中国这个社会存在问题,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共识。但是问题的根源在哪儿,有人认为在于人,于是致力于“国民性改造”;有人认为在于制度,于是致力于,推翻旧政权,建立新社会。但是,两者常常是互相牵扯的,鸡生蛋,蛋生鸡。一方面,有了好的制度,制度本身会培养出好的公民。另一方面,没有“新民”,制度如何建立?即使成功,没有“新民”,制度如何维持?
晏阳初认为:只要大多数中国人民仍然是“聋、哑、瞎”,军阀们就会继续为非作歹。“瞎”指人民不能读书,“聋”指人民不知道国家或地方大事,“哑”指人民不敢指责和反抗压迫和。(第18页)
我的观点是那些干的理想主义者,无论成败与否,最后他们注定要失望。因为即便是成功,胜利的曙光也从未照耀在他们所梦想的那个光辉灿烂的新世界上,也未能照亮人类所有卑劣自私的阴暗角落,而是照在了一个人们所熟悉的平庸的地方,仍然需要食品杂货店和污水处理系统。(第10页)
所以,晏阳初试图从教育入手,逐渐改造土壤、培育种子,最终改天换地。一代很多乡建先贤,都如胡适先生所说,“以渐进与改革的手段来实现一个极为激进的目的”(第12页)。文明的整体改造,这当然是一个激烈的目的。不过,激烈的目的也可以通过润物无声的方式。建生自述:“我之所以能从一个的理想主义者转变为乡村建设的践行者,也是因了对教育的信仰。”(第11页)
我们正处于一个文明转型时期,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。这话现在非常正确。但是,如何转,怎样转,是个问题;乃至于什么是生态文明,生态文明是什么样的,也没有统一的理解。
我的工业文明批判常常被人质疑,没有给出一个可操作的方案。对此,我曾经采用尼尔波兹曼的方式回答:作为哲学家,我只负责提供方向,不负责提供方案;但是,你不能因为我不能提出具体的方案,而否定我提出的问题。当然,我也在努力寻找方案。只不过,这些方案仍然是方向性的。所谓术业有专攻,文明转型这样的大问题,不可能由一两个人提供完整的可行的蓝图。
我接触乡建这个领域不算晚,早先是出于情感。作为农民的后代,我在农村一直生活到上小学,对于农民和农村有天然的感情,也一直通过家里的亲戚关心着农村的现状。所以李昌平对总理说实话,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共鸣。此后,我开始关注“三农”问题,了解温铁军先生的工作。再往后,与温铁军先生有了直接的接触,认识了温先生的几位高足,包括建生。
大约2005年之后,我批判的对象逐渐从科学主义扩展到工业文明。我从垃圾研究出发,得出一个很强的结论:由于垃圾问题不可解决,工业文明注定不可持续;如果不能在有限的时间,转向新的文明,人类文明将会崩溃。文明的整体转型,包括社会转型,又不仅仅是社会转型。不久前,在一次未来哲学的小型会议上,陈嘉映先生听过我和刘华杰的报告,形容我们的工作,说有一种老虎吃天的感觉,不知从何下口。这也是我最初考虑这个问题时的感觉。方方面面,千丝万缕,盘根错节,牵一发而动全身,哪儿都可以作为起点,从哪儿下手都发现难以操作。
经过几年的沉淀,与同行的交流,我慢慢地找到了两个切入点:一个是教育,一个是农业。前者关乎社会意识,后者关乎物质基础。教育这个点容易理解,一个生态文明的社会,需要这个社会的主要成员,具有生态文明的基本观念。这需要通过教育,实现全社会缺省配置的重新建构。农业这个点可能会让人感到意外,但是很快就能想通。人总是要吃饭的,吃饭就需要农业,那么很简单,在一个工业化的农业之上,怎么可能建设起一个生态的文明!所以,生态农业是生态文明的前提和基础。从学理上,我从工业文明批判入手,转向生态文明建设,再转向生态农业建设。
但是,农业不可能脱离农民和农村而独立存在。建设生态农业,也需要重建农村、重塑农民。生态农业建设与乡村建设,就自然交会到一起了。
中国的生态农业实践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,有不同的理念,不同的思想资源。我关注较多,对我影响也比较大的有两支队伍。一个是蒋高明先生在2006年7月创办的弘毅生态农场;一个是温铁军先生在2008年创办的小毛驴市民农园。作为“三农”问题专家,从一开始,温铁军先生所关注的就不仅仅是农业的生产方式问题,而是着眼于农村、农民和农业三个层面。小毛驴的命名大有深意。作为温铁军先生的,建生的立足点在乡建之上。建生的博士学位论文《在地化知识与互助型社区建设》,就是一篇基于乡建实践的理论工作。作为生态学家,蒋高明的思路比较明确,就是以生态的方式进行农业实践。不过,很快,蒋高明也发现,生态的农业方式,也是在具体的社会意识中进行的。蒋高明同时变身为社会学家,开展农村调查。同时,也在对农民与基础官员进行生态教育。也在不知不觉中转向了“乡建”。
在晏阳初的时代,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尚未发生。所以当下乡建所要面对的现实,要多一个生态和环境的维度。在对于未来理想的预期中,也需要多出这个维度。
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工业文明的全面冲击,中国农村的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。晏阳初当年的问题依然存在,依然贫弱愚私,依然聋哑瞎,只是换了方式,换了形式。
多年前,看到有个地方,全村以拐、卖孩子为生,让我难以置信。前年,又看到新闻,农村的老年人率大幅上升。一位在城里工作的孩子回到农村,问他的父亲:“你到底死不死,我只请了七天假!”让人想象不出,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。在晏阳初的时代,农村的自组织力量还在,宗法制度还在,儒家伦理还在;今天,农民在自己的家乡失去了意义,青年人从小就习惯进城打工,与土地之间不再有天然的浓郁的感情,也失去了务农的能力。
草根已经开始烂了,草根下的土壤沙化了。与此同时,农村的自然环境也发生了巨变。在很多地方,几十年的工业化农业已经把农田变成了污染源。
在另一方面,农村不再有那么多的文盲,基础教育基本普及,村村通让大多数人家都有了电视,能够与城里人同步看《新闻联播》,看电视剧。大多数青年农民也都有手机,用微信;信息流动更快,更杂。但是,农民的基本信仰是什么?农民的基本愿望是什么?这需要通过具体的社会实践,才能有所了解。
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书里面建生本人的乡建经历和经验。他在投身乡建的过程中所亲身经历的种种事件,初闻匪夷所思,但又是当下农村的现实。不了解这些现实,就没有一个相对准确的对当下农村的判断,从外面来的志愿者,很快就会四处碰壁,不得不铩羽而归。我在康奈尔看过一个纪录片,讲述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大学生,在联合国某组织的安排下,来到泰国乡下的中小学支教的故事。影片中,这些志愿者很快就陷入迷茫。他们只有一个关于教育的抽象理念,他们对于未来的构想,都是基于工业文明的缺省配置的。同时,他们也不了解泰国农村的具体情况。我们现在有很多热情的青年,心怀善良的理想,愿意去农村支教,其实也常常属于这种情况。
我建议这些青年在去农村之前,能够读一读建生的书,自己先受到乡建教育,再去实践自己的理想主义。
建生在书中还有一些非常具体的经验,比如如何与乡村干部打交道,如何与农民打交道;如何建乡村图书馆,如何建乡村大学这些操作层面的经验对于其他的乡建人士,也会有借鉴和启发。
乡建人士大多是理想主义者,愿意为理想付出青春,付出终生。梦想像呼吸,须臾不可缺。梦想赋予生活以意义,梦想就是生活本身。建生不断追问:我们要去哪儿?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?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,失去了梦想的生活,是不值得过的。但是只有梦想,没有行动,梦想就只是梦。行动是梦想的翅膀,能够让梦想飞得高,飞得远。
《梦想像呼吸新乡村建设工作手记》,邱建生著,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
◎邱建生,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(海峡乡村建设学院)教师,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副秘书长,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总干事,爱故乡计划发起人,一直从事乡村建设的研究和实践。
◎该书介绍我国乡村建设的起源和发展,介绍了乡村建设思想和乡村建设哲学;介绍了农村现状及期待发展的问题,介绍了作者在乡村建设实践中的经验和实例。该书对促进农村发展,对更好理解和解决“三农”问题有建设性意义,可供参与新乡村建设的实践者、研究农村发展的研究人员参考。